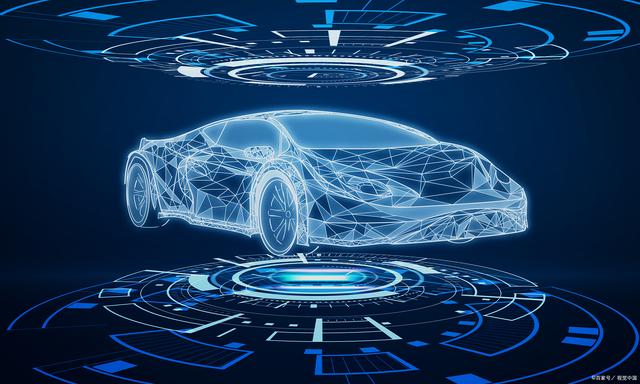作者像
诗歌,锻造在词语和灵魂的淬炼中
——也谈诗歌的个人化写作
• 张卫东 •
或许,就诗歌与诗的写作本身而论,“热爱”真的是“最好的老师”。而事实是,多年以来,那种写作的冲动主要还是缘于生存的压力和对现实的无奈,或者说在个人命运的遭际中,渐渐产生于生命里那些需要借助诗这个形式加以表达的情感律动,以获得生命对世界、对人与事的某种描述、想象和精神的释放与平衡,而所谓“享受”,只是一种说辞。如果说,这个过程延续至今形成了某种自觉,或从整体上讲作品产生了什么“质”的变化(就我从前的诗作而言),那实在是于有意无意中自然达成的。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往昔的、心理与文本意义上的“激情”与“想象力”正渐渐丧失,诗是越写越少了。
对于诗歌,我一直这样认为:完成一次写作就是完成一次和自己的对话,既是和自己对话,就应当说实话,说真话,服从于自己的内心,所谓“诗由兴起”,由心而出,向心而归,这似乎更贴近诗的本质,虽然,这是十分个人化的事情。但是,一个成熟的诗人应当知道,在现实的语境下,真正考验诗人功力的,是一种语言对言说对象的准确切入与重构、转换和综合的能力,包括修辞和用典,必要的变形与晦涩……尽管这一切都得通过每一次具体的写作去达成,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诗人,一首诗,又必须对此有所超越,在服从自己内心的同时,上升到某种更大视角的观照,才有可能抵达当代诗歌应有的宽度与深度,驳杂与丰富,才有可能达成写作的殊异与有效。
可以说,二十多年来,诗的写作在我身上似乎早已成为生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当然,也仅仅是一部分)。而我写诗是不择什么时间地点的。我时常于闲暇之余观察思考、想象着一些问题,一些人与事,或工作间隙、或阅读当中、或散步、或品茶、或与人交谈,包括在旅途中,在火车上,……甚至早起或深夜醒来,都有可能突发“灵感”而掏出纸笔,信手写来。这就是我的写作状态。这是生命赋予我的,而不是其它。我写,是自然而然的,哪天不写了,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责任”、“使命”之类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对诗的“担当”(也没有那个水平和能力)。至于那些什么经提起“专业”编辑的评审或“权威”诗评家推敲一类的标准,在我这里更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我的写作只对我自己负责,我认为满意了,我的写作标准也就达到了(这也许出自于我性情中与身具来的顽逆和偏执)。随着后来写作的持续与深入,我认为这是需要重新认识,并加以修正的。
诗是什么?“诗就是专主抒情的高级语言艺术。是用心灵化的意象语言实现对客观世界的重新整合,以最直观、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以获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绝对自由。”(熊国华《诗的沉思》)由此说来,诗所要表达的就是诗人凭借语言这个载体(或称途径),以诗这种特定形式为媒介,发自心灵深处对客观世界、对生活的感悟、联想和再造;其目的是通过这种表达,使诗写者得到语言的淬炼,精神的愉悦和灵魂的提升。由于每个生命个体的局限和偏差,使之面对同样的世界和事物所引起的感悟和震颤的不尽相同,从而出现表达上的落差。另外,就技艺与形式来讲,每个人对语言的敏感或词语的把握及运用能力的不同,包括想象力的差异,形式构建差异等等,从而在呈现为诗的表达效果上的不同。而“精神的超越”,我理解为诗人对所感事物的联想所能达到的时空边界以及在哲理上所能达到的思维深度;所谓“心灵的绝对自由”则指出了内心对这种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与准确性。实现了这些,我以为也就抓住了诗的本质。所以,就一个诗人,一首具体的诗来讲,为何而写,写什么,怎么去写,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他个人。
既然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有人甚至将写诗称为“语言的炼金术”,所以,我也常常思考写作中的技艺问题。所谓“技艺”,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在具体写作中由难到易、由浅入深,自然而然提高的。简单的途经便是:多观察、多思考、多读、多写、多练。试想,一个俗世中人,就个体生命而言,经历着别人无法替代的经历,感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感觉,对整个生活过程的感悟只有自己最清楚。既如此,我以为诗的写作首先应是服从于诗者内心的,所谓技艺也应是服从于内心真实的表达的。诗人是“语言的炼金术士”,这与“语言的工匠”是应有所区别的。我以为前者赋予的应是“灵气”,后者则是“匠气”,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一个诗人的写作能走多远,持续的写作能使他的技艺达到什么程度,除了所谓语言的“天赋”或后天的“努力”外,我想,更主要的是,他对诗的写作的整体认识、把握、及语言的应用能力。但这也是十分个人化,因人而异的。或者说,一个人的诗究竟能写到什么水准、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全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与修为。不管怎样,既然要写,除了真诚,对语言的探索,对语言的“敬畏”之心是必须要有的。这是一个诗人的专业素养,更是一个诗人应有的责任与良心。显然,这很难作到,或者说很难完全作到。
多少年来,我一直过着和众多普通人一样平凡、琐碎的生活,经历着和别人一样的“甜、酸、苦、辣”,“喜、怒、悲、欢”。如果说生活对个人来讲还有复杂、独特的一面,那就看你是从什么角度去观察、体会、认知你周围的人和事了。当然,每件事物都有它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或多或少的从个人生存遭遇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从而产生出各自不同的观点、立场及行为方式。但从对事物认识的正确与否的角度上讲,他们彼此的本质和规律应当是一致的(尽管常常不一致,常常表现出很多悖谬)。这就从某种层面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可能的场景和空间、可能的标准和参照。但这应是心灵与生活、生命与自然真实碰撞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而诗人在我看来就是一群对分行文字、对语言有着特殊兴趣或“天赋”的人,仅此而已。所以,就文本意义上的写作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吹嘘、标榜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抱怨、后悔的,那是你自己的选择,甚至就是你的宿命。因为就你的生命而言,不写不行,那你就写好了,别在乎其他的。更何况,一首诗写得好与不好,对其感受与评价,也是非常个人化,因人而异的。
有朋友曾这样评价我的诗:前期(99年以前)诗作语言上偏重抒情,唯美,呈现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特征,形式上则受第三代诗人影响较重。后期(2000年后)则转向以叙述性语言描述为主,有“批判现实主义”态势且词语高蹈,而思辨,置疑,追问则贯穿于我前后写作的始终。也许是吧!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哪种特征或态势,在我看来,同样是要服从于内心表达的需要。其实,“抒情与唯美”是我写作始终遵循的目标和原则,因为诗就是用来抒情的(当然不是浅表的,做作的,无度的滥情),诚如我一贯的认为,“喜、怒、悲、欢、忧、思”都可以抒发。只是,他应是自然的,而非矫情的,是富于张力的,而非粗浅的、直白的,重要的是,表达什么,怎样表达。我想,语言既然入了诗,无论怎样都应给人以美的感受,美的词语,美的含义,美的张力,美的韵律,美的呼唤,美的希翼……。说到“浪漫”,我想,诗人的内心,诗的写作本身就富于浪漫色彩,这是自然而然的。而英雄侠义,田园牧歌,古代隐士般悠然逸得的怀古情节也是不少诗人心弛神往的,尽管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多少显得有些矫情。至于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实在是友人对我的溢美了,想必同我那时的阅读有关吧,那多少对我当时的写作有些影响。说到“后期逐渐转为以叙述性语言描述为主”,我想,这一方面与年龄和阅历有关,年逾五十,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而性情与心跳却渐渐慢了下来,也许选择舒缓的叙述性语言节奏更适合我现在的状况;另一方面,这又属于形式与技术的问题(当然,也不完全是)。即使在我后期的写作中,“抒情,唯美,浪漫”也仍然贯穿于我的始终,或许只是更为隐忍、谨慎些了。同时,我也在继续的写作中努力尝试着以基本言说气质不变为根基的形式上的变化,以避免因长期写作所带来的对写作的厌倦。总之,变于不变,怎样变?还是围绕着内心需要,为内心的表达服务的,只是由于我的愚笨,总是做的不好,但对于服从内心的表达来讲,我认为这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就心灵而言,“技术永远不会消灭文学,正如它不能消灭宗教一样。”([美]艾萨克·辛格)。说到“思辨”,我就更惭愧了。因为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更疏于深思,不求甚解,权当友人对我的鼓励和高抬了。而“置疑”“追问”,“批判现实主义”,我不敢这样给自己归类。也许是生存环境和状态使然,也许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潜在的某种写作立场和向度。现实中具体的生活总是时时袭扰着我们,许多具体的人与事需要我们作出回应与选择。那么词语的“高蹈”,我想当属于我与身俱来的性情所致。于人于诗,我确实是较为容易激动感奋的,这在我的诗中肯定有所凸显,所谓“诗如其人”嘛。
都说诗人总是追求完美,是理想主义者,而精神上的“个人理想主义”往往在现实中又难以实现,甚至碰得“头破血流”,所以,诗人同时又是悲情主义者。有时,我就想,似乎不应对我们的写作赋予太多崇高和形而上的色彩。那种过分沉湎于个人理想主义的执着,有时反而会损伤写作,这是就文本而言。另一方面,它似乎总是暗含着某种潜在的野心,无论向内还是向外(虽然我们表面总是否认这一点),这就不仅仅是“热爱”、“虚荣心”的问题了,尤其面对当下“诗江湖”的混乱与喧嚣,这样的宣称极易使我们的写作陷入巨大的虚无空洞之中而难以进行和延续。事实上,这种“崇高”,这种“理想主义”的所谓“英雄”情节常常因过分的渲染而显得荒诞和滑稽,给人以矫情、虚妄和可疑之感。而对于写作本身,深处内心巨大的孤独和寂寞旷野,从心理学上讲,长时间的劳而无功与茫然无措,接踵而至的就是厌倦。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看,那种总是以所谓“崇高”、“理想主义”标榜的,动辄冠以这条“道路”,那种“理论”,这面“旗帜”,那个“主义”,总是以所谓“良知”、“道德”、“公理”、“正义”、“完美”……等等而引发的个人野心的膨胀及对他人的无端指责、漫骂或误导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自己就曾因此而时常陷于巨大的无奈和悲情之中,这是很不好,很不健康的。究其动因与本质,还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非理性的个人专制主义作祟,这种因素哪怕只有一点点,其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真正的崇高与理想主义应是对服从于内心的坚守,而非口头的标榜,更非自我或借助外力的炒作与哄抬。一个清醒的诗人应自觉撇弃一切与写作、与诗歌无关的虚张声势和别有用心的鼓吹与标榜。尽管就人性固有的弱点而言,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应当努力学会沉下心来,坚守孤独,稳住自己。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已走过了近百年的时间,新时期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也已经历了三十余年,纵观整个过程,有过喧嚣,也有过沉寂,有过轰轰烈烈、门派林立,也有过相互疏离,冷冷清清。虽然时至今日,仍有人在不时回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诗歌运动那种火爆的场景,甚至渴望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再掀一场这样的“风云”,但毕竟时过境迁了。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八十年代中国诗界所发生的一切自有它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时“高手”云集也好,“英雄”辈出也罢,然真正属于沉毅内省、隐忍克制,讲求技艺,经得起推敲、能让人为之动容并铭记的诗人诗作又有多少呢?诗在当时泥沙俱下的漩流中就象一个受到过分惊吓而又摸不到堤岸的孩子。而当下诗歌的边缘化与过分游戏化似乎更使诗的存在和力量显得那么微弱、那么“不堪一击”,其功能在商业与物欲化的今天是那样的“无用”,“诗人”这个词从来没象现在那么容易被人忽略、遗忘、厌弃甚至耻笑……。原因在哪儿?症结在哪儿?我想除了当下的某些社会因素外,更多的问题恐怕出自于诗人自身及他们的作品吧,况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与成就岂是那些浮燥、喧嚣的“运动”、“争斗”、或过分的“游戏”与“娱乐”能够实现的。我只知道诗在我们每个爱诗者心中,在我们认真默默的写作中,并永远属于“无限的少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后工业化、信息化的今天,在社会生活与分工更加复杂、多样、多元化的当下,诗人,诗歌被“边缘化”并没有什么不好,而诗歌的过分“游戏化”,“娱乐化”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置疑,一个真正钟情诗歌,严肃意义上的诗人,应当把精力更多的用于诗的写作本身,而不是过分沉湎于诗的“游戏”与“娱乐”,要学会享受写作的孤独,诗的孤独。因为,我们终归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正如布罗茨基在《取悦一个影子》一文中所言:“如果说一位诗人对社会有任何义务,那就是写好诗……。如果他完成不了这个职责,则他就会坠入遗忘”。何况,“社会对诗人没有义务。社会按定义是大多数,它认为自己有读诗以外的其他选择,不管诗写得多好”。
其实,何为诗人?诗人何为?这是荷尔德林早就给出并试图回答的命题。诗人南鸥以他的诗性立场与实践给出了如下诠释:“诗人应该是一个民族语言的智慧与光芒的开掘者,精神与情怀的捍卫者。他所闪耀的独立意识和精神品格,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元素。他是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他应该引领和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品格。这就要求诗人保持一种独立、自由、责任的精神禀赋和人格姿势。也就是说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微妙而隐秘的,是一种在隐秘的对峙中燃烧,在燃烧中对峙的关系。而正是这种隐秘的对峙和燃烧,赐予诗人高洁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守护神,诗人的天职是捍卫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品格,因而,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我认同这样的文字。
同时,我还要说的是,那些总是试图以权威大师自居,或总是以某些权威、大师的作品为模式,企望从异国哲学、艺术、理论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般地来为自己的写作寻找依据并建立自己不切实际的、空泛的诗学理论,从而把自己塑造为英雄或“诗坛舵主”以争得所谓“话语权”的想法,对于当下中国诗歌多元化的写作格局而言,是虚妄滑稽的。真不知道,多少年来那些争吵于中国诗界的、种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观点和派别对于我们个人化的写作来讲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说某个人的诗写得好,肯定是指他的某些作品从形式到内涵,从技巧到语言打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而绝不是指他善耍嘴皮子般地空谈理论或卖弄知识等等,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人最大的知识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诗就是诗,她的“好”与“不好”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要说,任何诗歌理论和作品对我而言,只能是参阅、借鉴和欣赏,绝不是因袭和复制,更不会成为向他人玄耀或争名逐利的资本。
我们生活在这个严酷的现实中,人们所遭遇的压力和痛楚决不仅仅来自于生存本身(物质方面),它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精神的失衡。一方面人们在紧张劳顿的奔波中,在危机四伏的处境里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渴望沟通,渴望理解,渴望获得某种心理的慰藉;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顾忌,出于某种权力、地位、利益和偏执的自尊,在表面开放的个性张扬中将自己真正应该并渴望表达的真实深锁心底,从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一个庞大的人格扭曲、心理错位的怪圈,并长久地制约着人们正常的精神追求与人际交流(这种情形也必然渗透并影响、反映在当下的诗界)。看看我们的周围吧,每个人都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精神的释放与平衡,都在希望让自己活得快乐一些,这本没有错。可是,在金钱与商品意识的驱动下,功利、浮燥、媚俗、快餐式的表达充斥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消磨、麻痹、瓦解着人们的神志和心灵,人们在疯狂地欢悦中追求着一种简单、低级的快感,人们在猜疑、妒忌、诋毁、俸承和不信任中活得那样虚假、孤独、机械和疲惫。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事实。当然,我们选择了诗。当我们为自己所钟爱的诗歌孜孜以求,如醉如痴的时候,当我们甘愿成为“无限的少数人”的时候,我们不应当相互勉励和支撑吗?我们不应当以我们各自的写作,以我们透明洁净的、满是真势与美好、满是爱意的诗行带给人们以莫大的启示和抚慰、愉悦和鼓舞并使我们自己的灵魂在这孤独艰难地攀爬中得以超越和升华吗?
所以我要说,诗的写作对于我们决不仅仅是情绪的渲泻、琐事的陈述和文字的堆砌,更不是把玩于口舌和纸上的游戏。诗的写作是一种灵魂的昭示和人格的凸现。从诗学的角度看,她是一种集艺术底蕴、思想感悟和语言技巧于一体的心灵体验;她所展示的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历程;她所要实现的应是对道义、良知,对真善美呼唤,对无数个体心灵的抵达、抚摸、叩问、呈现,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关爱和颂扬;她要拒绝的永远是低级的把玩、功利的追逐和恶意的诋毁。这,或许就是诗人的责任,是一种坚守,更是一个诗人的福分。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要求诗人必须成为生活中的“完人”,精神上的“圣人”。在物质社会里,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诗人也需要维系其生存的物质条件,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离不开衣食住行;也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特征及要求;也会面对现实身不由己的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也会在生活中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失误,这都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当处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纠葛时,他该怎样去面对、处理这一切。这显然有个追求向度和方式方法问题。我认为,在当下市场经济与商品社会林林种种的诱惑与挤压下,在信息革命和后工业文明空前发达的今天,作为真正的诗人,一方面应当正视这个严峻局促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应当泰然处之,并“努力在写作过程中达成一种自觉意识,即通过写作使自己的灵魂永远向着美好的精神彼岸驶进,从而实现意识上对困扰于‘小我’世界的种种烦恼痛苦和世俗观念的漠视、消解和超越,向着人人的、与自然宇宙融为一体的‘大我’境界的不断靠进和提升。”(孙文语)尽管这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但我们既然拿起了诗笔,就应当作出这种努力,真正的诗歌只有锻造在词语和灵魂的淬炼中。正如沙士比亚所说“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气节。”
历史是什么?就是一个不断更新和淘汰的过程。诗的历史也是如此。一个诗人、一首诗,要有勇气承受这个过程。要写,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写。不虚妄、不矫情、不图名、不逐利,就是我所理解的写作的最高层次了。真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人格与诗的统一,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让我们共勉吧。 201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