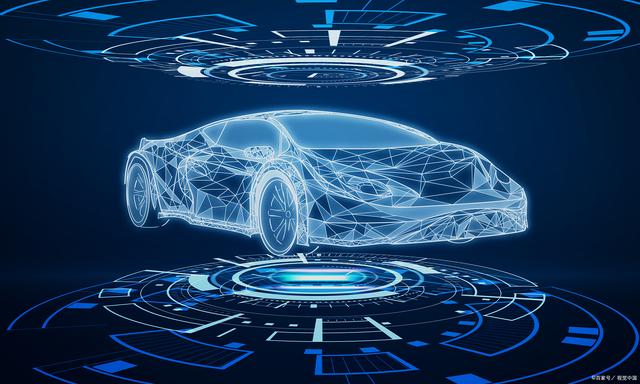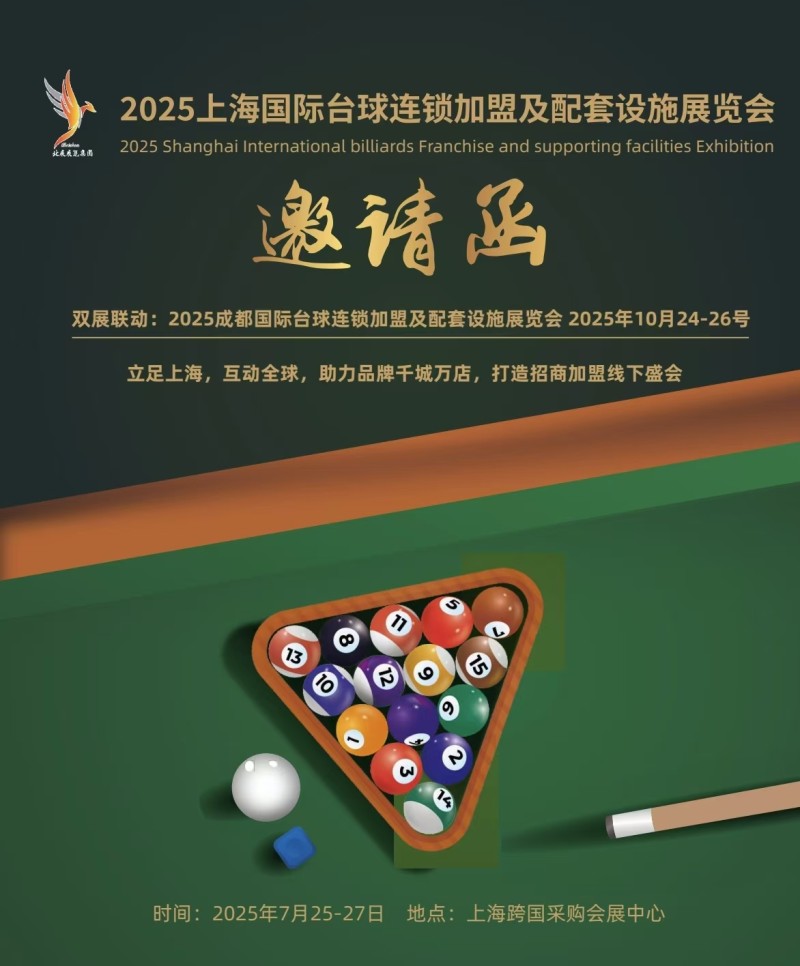9月15日是世界淋巴瘤日。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淋巴肿瘤内科教授朱军的诊室里,“淋巴瘤”是一切对话的关键词。但与这略带灰色调的三个字不同的是,朱军的诊室更像一间“聊天室”,所有的对话不疾不徐,又透着明朗的色调。他说,自己是帮淋巴瘤患者“卸包袱”的人,这个“包袱”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

每天第一项工作是“会老友”
“身上长了好几个包包,可是脸上一个都没有,你应该谢谢它。”
“(化疗后)头发少了,包包小了,打个平手!”
“别着急,我们现在只用了‘红缨枪’,‘重武器’还没用呢!”
这是朱军和患者的对话。
朱军是重庆人,虽然离家多年已听不出太多乡音,但川渝人乐观的性格还是会不自觉地从他的话语间透露出来。尽管身上扛着科室、医院、社会等多重责任,但最让朱军觉得踏实、快乐的地方始终是临床。跟在他身边20年的学生、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副主任医师张晨对朱军的习惯很清楚。每天例行查房、每周1~2次全科大查房,他一次不落;科室患者周转快,每天有六七名新入院患者,他都会一一过问。在淋巴瘤科的医患“心语墙”上,朱军那张心形卡片上写着:“一生只做一件事,就为你们当卫士。”
最近几年,朱军觉得自己这个淋巴瘤科医生做得“有点骄傲”。淋巴瘤是我国常见的十大肿瘤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近年来,淋巴瘤发病年增长率为7.5%,是目前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淋巴瘤诊治水平有了飞快的进步。朱军说,以北大肿瘤医院为例,这期间,淋巴瘤患者五年生存率提高了约5%~10%,目前达60%以上;其中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更是达到82%,和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持平。
这些年,朱军对学科的发展感同身受:“作为肿瘤科医生,现在我们的患者经过治疗,有一多半都能被治好、活下来,我们看着他们上学、工作、成家、做父母,真的很开心。”
每天早上7时半左右,朱军会准时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要处理的第一份工作多是“会老友”。这些“老友”是朱军曾诊治过和正在复诊阶段的患者或家属,他们远道而来,多数只为见个面、问声好。很多和朱军一样的淋巴瘤科医生背后都有这样一支患者队伍,随着发病率、诊断率和治愈率的提高,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朱军和同事们为他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诊疗和照护,他们之间也相互支撑、彼此温暖着。
要能把住自己的"药瓶子”
“淋巴瘤‘好治’。”20多年前,这曾是朱军和同行们之间一个苦涩的玩笑。几十年来,淋巴瘤的治疗曾一直沿用有限的几种化疗方案,没有太多好办法。
那时,朱军刚刚完成在国外的深造归国,进入北大肿瘤医院。刚创建的淋巴瘤科,患者少、效益差。和现在平均住院日仅为2.3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一名患者在病房能住半年。但即便这样,朱军和团队也认定淋巴瘤领域,而且坚持要把它做好。
把专业做好,首先是要对患者好。张晨说,这种一心一意为患者着想的理念,是科室一代代传承下来,并浸润到团队每个人的行动中的。小李(化名)原本在一家医院长期就诊,因为不放心,来到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恰好,他挂号看的两位医生都是朱军的学生。就诊后,他感叹:“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如此全面、透彻。虽然生了病,但我却在北肿找到了踏实的感觉。”就这样,良好的口碑在患者之间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患者因为信任找到朱军和他的团队。
进入21世纪,国内外淋巴瘤治疗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关新药和治疗方案越来越丰富,全世界对于淋巴瘤的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淋巴瘤的分型也越发重要。但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淋巴瘤治疗领域主要依照国外相关临床指南。朱军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众多专家组成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制定相关诊疗规范,提升淋巴瘤诊疗水平,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2018年,朱军联合团队牵头完成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倡导下,通过多学科协作,在疾病诊治、人才培养、分级诊疗方面“多管齐下”,力争为我国淋巴瘤诊疗实践制定严谨的“规范”。在此基础上,朱军组织建立首个国家层面淋巴瘤标准数据库,从而更便于了解我国淋巴瘤的流行病趋势、特点和规范化诊疗现状。此后,朱军又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首次报道了中国淋巴瘤疾病负担,分析淋巴瘤在1990—2019年的变化趋势,为疾病控制、政策制订提供了可靠的流行病学数据。
2019年11月,一款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以“突破性疗法”的身份优先审评,并以早于国内的时间在美国获准上市。
朱军回忆,过去,几乎所有的抗肿瘤新药都要从国外引进。患者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有时三四年,有时超过十年都盼不到。即便患者熬过了等药的那些年,进口药的价格也长期居高不下。
2015—2021年,朱军团队共推动16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牵头或参与开展约130项国内和国际新药临床试验。“我想,我们不仅要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还要稳稳把住自己的‘药瓶子’。”朱军说,以往我们缺少原研药时,很多进口药长期处于“独霸江湖”的状态。获批上市后,它们有的长达20年不曾降价。但近几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国家在政府治理和健康管理方面的水平和能力。
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8.2岁,继2020年后第二次超越美国。朱军反复点着数据说:“我们有基础,也应该有信心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并在多个医药领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从“99086”到“211”
前不久,朱军搬进了新办公室,门牌号从“99086”换成了“211”。很多人都知道,七八年前,朱军把自己原来位于9层的办公室门牌号改成了“99086”,谐音“救救淋巴瘤”。当患者站在生命的悬崖边时,他曾无数次拉住他们的手。这些数字,是他作为临床医生直抒胸臆的呼喊。
而现在的“211”,朱军觉得也很好。他说,“211工程”是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重点建设工作,这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代号,代表着我们对国家科技、文化等事业发展的愿景。“新的变化,也是新的要求。”朱军希望,自己带领的淋巴瘤科能在行业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自己也能从一个好的淋巴瘤医生出发,帮助科室和医院站到更高的平台,催生更强的能力。
作为一名管理者,朱军时常把“院有品牌,科有特色,人有专长”挂在嘴边。北大肿瘤医院建院较晚,开办时,地处的北京市定慧寺一带还比较荒凉。面对当时国内肿瘤专科领域的众多“老大哥”,北大肿瘤医院相对年轻,建筑面积也非常有限。朱军常想:“我们怎么才能跑得再快一点,再靠前一点呢?”
他觉得,应该用特色专科来拼一拼:“胃肠肿瘤、胸部肿瘤、乳腺肿瘤、淋巴瘤、黑色素瘤等,我们希望,只要一提起这些疾病的治疗,北大肿瘤医院能成为患者的首选。”
想把专科和医院建设好,首先“要让人高兴起来”。朱军提倡,对患者的治疗应该从他们一踏进医院就开始。他重视医院场所和文化建设,希望通过舒适的环境和医务人员的专业关怀扫除肿瘤患者心头的阴霾。他说:“如果患者不满意,做什么都是给别人看的。”他主张通过人性化的制度和文化的感染力让员工得到尊重、有归属感。十几年前,他就带领医院率先实现了在编职工和合同制职工的同工同酬。
张晨说,在后辈中,朱军因为脾气好、记性好、口才好“圈粉”无数,他几乎从不跟患者或年轻医生发脾气。几年前有一次,当得知有患者是通过“黄牛”挂的号,他难过了许久,告诉患者下次直接找他就能加上号。门诊外,即便不是他自己的患者,他也能过目不忘;自己的患者来复查,他能把患者的病情完整地回忆出来。而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听过朱军《肿瘤学总论》课程的医学生,更是有不少都因为他超强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对肿瘤学科、淋巴瘤专业心生向往。
如今,正值北京的金秋。朱军想着,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他还有时间把医院新规划建造的康养花园布置得更美一些,用更好的品位和格调传递对患者的关爱。这一隅缤纷的天地,承载着他对患者、同事们和医院发展的美好祝愿。“我们会努力让医院的大门成为一道有光的门、有希望的门。”朱军说。

文: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通讯员 管九苹
编辑:徐秉楠 魏婉笛
校对:于梦非
审核:马杨 闫龑